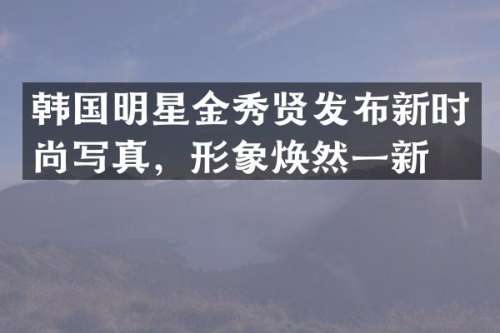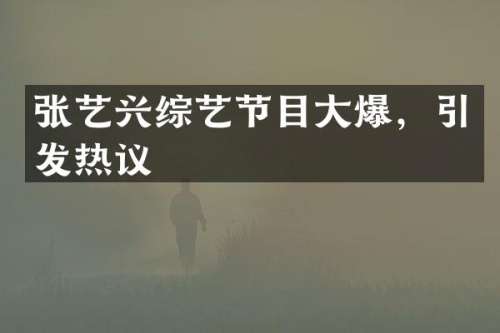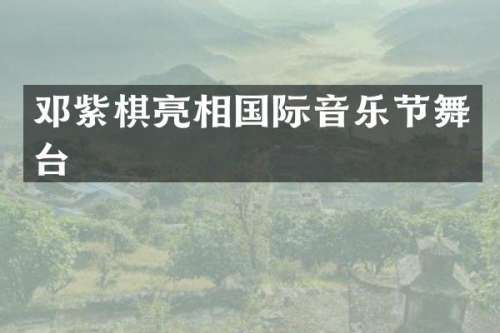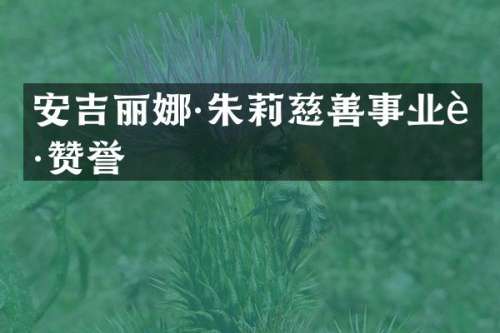“有时候坚强,约等于狠。”
“鹤岗宇宙”的边界是一道人墙
耿军导演如果不是对数字特别敏感,那可能就是对距离挺敏感的。作为鹤岗宇宙的奇点,他在采访中谈到,鹤岗是在黑龙江最东北的点,距离最西北的漠河、黑河,坐绿皮火车要20多个小时。这没什么,他是鹤岗人,了解这些很正常。他的另一次采访是在福建平潭,他说现在自己所处的位置距离海边7公里,而平潭距离海峡对面的新竹只有60海里。他没事爱溜达,7公里是散步半径,知道这个也没什么。
当一个人试图描述自己从哪里来,当下又身处何处时,大体总要先找到一个参照点,它当然可以来自地理划分,也可以来自经验体感。“酒店距市中心步行只需10分钟”,类似这种。但被耿军“偶然”选择的参照点,是光荣的边界而非中心。
鹤岗宇宙的边界是什么?在北京、纽约以及未来在哈尔滨拍的片子,还算不算鹤岗宇宙?我觉得算吧。鹤岗宇宙的边界一定不是地理上的,它可以约等于耿军关心对象的边界。“正常人”,没意思。
《轻松+愉快》中吐字不清,一个月吃两次带鱼的小二;到了《东北虎》中给人送礼还是炸带鱼,又展开了副业卖梯子,他算正常人吗?诗人得过精神病,他算正常人吗?中学老师徐东没有精神病,但是他大雪天举着喇叭站在儿童乐园门口卖诗集,又还给杀狗一个下跪,算正常人吗?
影片剧照
如果衡量的边界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医学,精神病人肯定不算;如果边界是卡耐基的成功学,《东北虎》全片,的欠债的;抓的当的,恐怕也没一个算。如果边界是法律,砸车的几位大哥也不算了。但如果边界是耿军划定的,他们都是正常人。因为现代医学和法律所划定的边界是为了现实社会的秩序,是为了更多数人的安全。但是在电影中,在小小的鹤岗宇宙中,耿军偏要让他们自由。
与其说重要的是对边界的观念,不如说那是因为边界所关涉的东西,它可以是我们因人而异的一种判定,什么才是所谓“绝对的”东西。对耿军而言,自由应当算是其一了。那么既然是边界,也总该有点什么是耿军划定之外的东西吧。大概是死亡、是暴富,是任何因为失去自由而导致的患得患失。是与寒冷带来的清醒割袍断义,扑向温暖的幻境。所以,耿军能准确描述出边界的只有鹤岗这座城市。对于鹤岗宇宙,如果有天耿军的那些“漂亮的”演员们不再需要寒冷了,耿军自己也渴望被温暖环抱了,鹤岗宇宙也就不存在了。它的边界其实是这样一道人墙。
影片剧照
《东北虎》中的“一般等价物”
文化人复仇和“一家之主”捉是《东北虎》中的两条线索。站在两条线索交叉点上的男主徐东,挺倒霉的。生活中一下出现了两个“意外”,寄养的爱犬需要复仇,老婆又因为发现而加以威胁。但其实这两件事都不算意外,准确地说,它们是徐东日常生活中的“溢出”,是一种例外状态。
什么是例外呢?它就是秩序与混沌的交界处。原本徐东的生活是有秩序的,尽管影片的一开始他就自我定义成为一个人老色衰,经济衰败,稳定的家庭也只是看似而已的人,但是他的生活依然在某种平稳的规则下运行。他是名初中教师,赚的不多,但尊重文化;他有情人,但也妻管严,没想离婚;他不算得意,抽烟发呆,但心里没有仇恨。
影片剧照
但是当两个例外出现,这种规则突然被悬置了。徐东的那些,闷着打不着火儿的愤怒和恐惧一下被点燃了。他必须放弃惯有的规则,临时决断。因为这两件撞在面门上的急事儿必须解决,且只能靠他自己解决。解决事情的“必要性”反而使得徐东赋予自己某种“神圣性”,他要重新创造一套规则。
这套规则的建立从他牵着狗去市场,被询问八块钱一斤卖不卖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了,直到还给杀狗马千里一次下跪,还有对个人生活的强制“矫正”,他建立规则,实际上就是在明确并信任一种一般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是货币的本质。从物物交换到商品经济,货币经历过贝壳、金银、纸币等很多形态,但它们共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欲望的延迟满足。是因为即时的交换不再可能,生产力的提高也使剩余出现,一般等价物才有意义。这是钱能解决事情的世界,价格可以用来标榜价值。但这不是徐东,也不是追着马千里的亲戚们,也不是小二,也不是片中所有人的世界。
张志勇,饰演马千里
他们不是可以被抽象为“人口数”进行计算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完全不统一的,完全没法用钱来代表的一般等价物。那就是公平。怎么算公平?马千里觉得,杀了徐东的狗,还一枚陪了自己十几年的戒指算公平,如果再商量商量,牺牲一点尊严,跪一下也可以,但磕头不行,那就过了那个他认为的公平的点。徐东去马千里家,看到他被追债的砸碎了玻璃,动了恻隐之心,价值四万块的金链子,他不要。因为他觉得马千里欠他的也不是钱,他复仇也不是因为狗值那么多钱,用钱还,对谁都不公平。
所以这次“文人复仇”注定失败,因为如果一般等价物是公平,两个各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怎么可能达成一致呢?所以只要工程款追回来,马千里和亲戚们的债很快就能解决,因为那是一种被化约的统一,但马千里和徐东的债永远解决不了,因为他们压根没打算放弃差异性。
影片剧照
质感让色彩缴械投降
东北的冬天,从飞机上俯瞰,就是灰色的。它其实有很多颜色,雪的白色,土的黑色,树干的棕色,但是拍进电影里,它还是灰色的。因为镜头是一个色彩放大镜,而我们看过的大部分电影也远比《东北虎》花花绿绿太多。色彩丰富不见得成为一部电影的加分项,但空旷、极简的背景拍好了,真的更容易突出演员本身的质感,这种质感让色彩缴械投降。
影片剧照
在《东北虎》中,这种质感就是局限性,每个人物的局限性,丛林之王东北虎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现实主义电影中角色的局限性都足够明显,他们时常也会拥有过多的自由而变成了生活中的英雄。在耿军的电影里,个体的自由是风筝,但始终有一根线牵着,叫做人的主观性,角色再如何挣扎,都无法越出他的主观性。
“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一棵花椰菜。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连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这句话来自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东北虎》中的人物质感,就在于它让每个人,都是具体的,有名有姓的谁谁谁,然后在耿军的鹤岗宇宙中,如其所是地活着。
影片剧照
他们先是信任别人。妻子当上了侦探,从她觉得嫌疑最大的女性开始查起,她也去求助了朋友中的有钱人,无果。丈夫为爱犬,打电话义正严辞地问对方,你就说你在哪吧,然后他找到人,无果。追债的找了公司,最后还是亲自面对面理论,无果。
在事情刚刚发生时,他们像相信飞机会准时起飞,火车不会出轨一样,把信心建立在自己对于与他人关系的判断和操控上。然而人性是残缺的,人道主义只有在人的定义和人的关系得以整全时才有意义。他们终于接受了自己对于他人判断的局限性,回归到自我需求本身,重新制定方案。
寒冷让人清醒,也更珍惜温暖。在寒冷的地方,人的每一个动作,好像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迟缓,但意识却是想通的。在那些不说话或者话里有话的时候,《东北虎》里的他们站在边界处,提溜着寒冷,彼此支撑,然后温暖。
影片剧照
《芭莎艺术》 耿军:
(采访:荷大齐、黄金狗)
耿军,导演,1976年出生于黑龙江。2002年开始拍摄电影,作品曾多次入选国际影展。剧情长片《烧烤》入围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新电影单元及鹿特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剧情长片《青年》入围罗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4年以剧情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获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2017年《轻松+愉快》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并获第54届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奖等四项提名。
《东北虎》导演,耿军
芭:可以聊聊《东北虎》这部影片的创作动机吗?
耿军:2000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鹤岗那个城市很小,有一个中心站,我在大年初二还是初三的时候,在中心站碰到了徐刚(《东北虎》里饰演诗人罗尔克的演员),他在那等车,我说你是去走亲访友吗?他说不是,他要去新华那边找个人,那人他把我狗给弄死了,他要去“弄”他。当时,下着小碎雪,这样一个男人穿着皮夹克儿,头上、毛领上落的都是小碎雪在那等那个中巴,中心站到新华镇要40分钟,这40分钟的路程就是一个奔向他要复仇的那个人的路程。我们在那见完面之后,这个场景就总浮现出来,我们脑子里边很多记忆都是沉睡的,有的时候碰到这个人了,这个沉睡的记忆才能被唤醒。
写剧本是2012年的事,我就从这个场景作为开头,写了这个剧本:碰到刚哥在那等车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我创作动机的源头,我写剧本是完完全全不打草稿,没有故事大纲,没有故事梗概,我抓住这个源头开始写人物关系,就一股脑就把剧本给写完了,写完之后修改的时间特别长。我从头写到尾,写成封闭空间才给别人看。因为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有一种不自知的状态,自己不够清晰,我们在逐渐找结构,逐渐在把其他的对手戏和人物给提上来,到后来逐渐修改,就变成了一条复仇的剧情线和另一条家庭生活情感危机的一条剧情线。
芭:为什么徐刚要去为狗复仇的这事会激起您的创作兴趣?在您看来触动到您的地方是什么?
耿军:我们俩是同岁,那个时候是2000年,我们都34岁。我们经常在现实生活里边讨论一件事——打架的成本是什么?第一成本是那一刻的体力,之后是财产,比如手表、手机、眼镜的损坏,还有身体财产,比如把牙打坏了;第三部分才是法律,这是社会规矩,你把别人打坏了,你得赔钱、坐牢,他把你打坏了你住医院,这是第三层次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打架的成本已经大部分都来到第三个层次了,就是你打人要付诸于法律,体力这个事和个人身上的财产的事已经不像青少年时期那么重要了。当整个环境、社会用法律来运行的时候,人受到的约束就特别大。所以当一件事出来之后,第一选择是怎么能和平解决,这是成年人的处理方式,这是理性的。
影片海报
但是这个人没有选择这样做,他还是用特别原始的办法,就是“你怼我一拳我必须踹你一脚”,你把我们家一个成员给弄死了,我必须得向你复仇。他连着找了四五次,那个人避而不见,就想等他先把火消了再谈。其实这个行为是打破了一个中年人的常规逻辑,把通常我们诉诸于理性的东西,推到了情绪上,推到了一个感性的点上,让这个人的行动产生一种冲撞感。这成为跳出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情绪,也是他血液里边血气的东西,它更接近于之前年轻时偏向江湖的、民间的方式。但是他本人又是个文人,他要复仇的那个人是个商人,是一个“江湖的人”。一个江湖人把一个文人拿捏得死死的,一个文人面对一个江湖人却未必捏得住,这个冲突就很有意思。
芭:影片中的主角的朋友,诗人,他的原型是您另外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在戏里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是戏剧夸张吗,还是现实生活中他也是这样的?
耿军:现实生活中他就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判决书”,比如一个人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持续的悲伤状态里,或者精神一直不太好,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被迫害患者症这种比较外化、直观的状态。当他去医院的时候,经过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有诊断书在了,这件事就会陪伴他的一生了。不会有人再开出一份证明:精神分裂症已康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病症会反复。所以精神病在法律上,是跟常人的判决方式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得了精神分裂症,他相当于被判了“刑”。
张稀稀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很正常的,他也可以正常写诗,微博上不定期还在发表他写的诗歌。我们喝酒吃饭聊天也都没问题,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暴力倾向或其他症状。但是他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作为一个确诊的精神分裂者,作客串门这件事就从他的日常里消失了,无论是他去别人家,或是别人来他家。所以他的生活完全被孤立起来,比他没得病之前更加孤独。我们是小学同学,一起长大,八九岁的时候就认识,只要一回老家我就找他,登门拜访。我让他去我们家他不来,他说上饭店的时候叫我,去家里不自在。
徐刚,饰演罗尔克
芭:刚刚说打架的成本——财产、法律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我们常讲用钱摆平,这是讲一般等价物是货币,影片里,马经理提出赔给他戒指的时候,他认为,这只狗陪你10年,那这个戒指也是陪我10年的,咱俩交换一下,徐东也没有答应。徐东心里的一般等价物是什么呢?在处理狗的这件事上,看起来是情感,他认为马经理是杀了他的家人,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去。但是他老婆说你把狗送走的时候,他可没表示要护着,好吧,我们就说他更在乎家庭,但他对婚姻也是不忠诚,而且应该是屡次的不忠诚,对吧?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我觉得挺复杂的,似乎只在碰到了某个极限的边界,它才爆发出来。
耿军:我觉得人就是复杂的,难道人只有单一行为?你说的忠诚是单一行为,忠诚是一种道德道德层面的东西。你的这种分析对我来说全都不成立,他面对狗的第一前提是想找一个好人家养着,过几天来看你,这是第二前提。个人在家庭生活里面情感里面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常态。你怎么去概括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太难概括了。
他心里的一般等价物是什么?故事的第一层心理等价物是公平。这件事在这个环境里边,一个普通人,这样一个小人物,要想拿到公平,你知道他要付出什么吗?一个文人去找一个江湖人要公平,他会要到吗?但是我们的戏剧情节没有那么进展,当一个文人被仇恨点燃了,他去找这个江湖人,他们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到第三次见面,文人看到江湖人逐渐走向人生最低的、最惨的境界的时候,恻隐之心来了,这个是人啊,我们不能那么刻板地去把所有东西归类,泛泛的归类可以,但那些都不是情感,全都是冰冷的东西。我觉得人是有温度的,是一个不会把所有事都能做对的综合体。
比如剧情里,徐东认为的公平是:第一步要先给他的狗跪下磕两个头,但马千里觉得这太伤我自尊了,要我跪下就跪了,为什么要磕俩头呢?我犯了错误了,我也是有自尊的。再比如,马千里把徐东约到了公安局。如果我在那个环境里,如果我是马千里,我也得约个安全的地方跟他见面,哪安全?派出所安全。但如果我是徐东,我也会动着残杀之念而来,我也会在包里边装个大管钳,把马千里撂在这儿,但是这个见面的场景在派出所门前,后边就是法律。我觉得这种冲突,特别“人”。
影片剧照
芭:刚才导演也说了,剧情里有两条线,一条线男人线——马千里和徐东、诗人之间的复仇和纠葛,另一条线是女人线,围绕马丽饰演的角色、徐东的情人的故事。但是您之前的戏里边关于女性角色的描写,笔墨并不是非常多,她们通常会作为一个符号出现在戏里面。那在《东北虎》这部影片里,女性角色的比例变得更多,尤其您还启用了一个像马丽这样的知名演员作为女主角。比如说这两个女性角色都说了比较重要的台词,女主角说:“有时候坚强约等于狠”,女二号也有一句词:“徐老师,伤感,没意思。”可以聊聊您通过这条剧情线的设置,想要表达或者传递什么呢?
耿军:我之前的电影里边女性角色确实非常少,我们也会聊这件事,我没有特别充足的素材能把以前电影里边的女性角色给描写好,我没有那么多的体验,也没有那么多的认识。真正认识的就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单一工作的、文化类的,这类人,她们其实是老实本分得生活,两点、三点一线的那种,他们的情感故事被很多作品都表达过。当写到《东北虎》这部电影剧本的时候,我的人生阅历跟之前相比已经丰厚很多,我在家里边跟同学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也听到很多家庭内部的情感关系的惊悚故事,那个才是真正的家庭内部的两性关系的故事,当我知道这些故事多了,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些支点,同时也发挥了想象力。他们同时也在互相塑造,女主角去找他老公之前的相好过的女人,她觉得那些都是我掌握的,通过这部分情节就能看到徐东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当她发现自己扑空了,她就去求助,求助也未遂。反正到后来还得自救,女主角的行为,对于任何一个丈夫,其实都会被准确打击的。
情感本身是特别有魅力的,大家都想得到好的情感,我们想有一段好的情感,想让这个情感特别稳定,想舒心地过日子,互相关心对方,在这种美好的向往种,组成了一个家庭,之后人们发现事情跟之前想的不一样,那怎么才能把它扳回跟我想的一样?这个战争就开始了。
人们对情感的向往、对情感的防御,构成一种内部的挣扎,我觉得它就是当下家庭里边最常见的、需要我捕捉的东西,所以我写了这样的情感戏。我想把日常的东西写出来,把波澜写出来,把对抗写出来,把那种忍让也写出来,走向宽容也能写出来。其实是有点野心,用我自己的方法,捕捉当代的情感,同时我又希望可以有点幽默感。
《东北虎》导演,耿军
芭:关于东北虎的隐喻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一个19岁的东北虎?
耿军:这个特别逗,我自己家那边,鹤岗动物园里,在我小的时候是有熊、老虎、狮子,还有鸟类。我们那个动物园前几年有一个公众号,是写鹤岗的公众号里我最喜欢的一篇,写的是我们鹤岗动物园里的动物,那只熊已经32岁了,它退休了,就不再跟大家见面了。我就想,这是我小时候见到的那只熊,是我爷爷领着我,后来我父亲领着我去看的那只熊,我们有三四代人都见过这只32岁的熊。在这个环境里,圈养的老虎最大年龄是25岁。熊32岁了,老虎19岁了,有一种年华就像炮捻一样已经燃烧到了一个关键节点,这个点能不能用冬天的寒冷或用水给它掐灭,让它先停一会儿,东北这种特别寒冷的天气是不是能让衰老得更慢一点?
我特别喜欢逛动物园,2012年我在上海动物园,我正好身上背着一台摄影机。也有一只东北虎,我就拿摄影机去拍它,拍了40多分钟,那只老虎所在的坑挺大,当那个摄影机推上去,我才能真正看到它的表情和眼神。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么凶猛的家伙,森林之王,就被这个坑困住了?出不来了?一点招儿都没有了吗?就在这里休闲着,在这等着人扔给它鸡或者牛肉。这只老虎被困住了。我的电影里边的人也是被困的状态,其实是互相一个映照。
芭:东北虎19岁,它被困住的、被圈养的同时,它也能活到19岁,而野生的老虎应该是活不了这么久的。您也有这层意思在里面吗?
耿军:它凶猛,它被困住,它安逸,它被观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互文,都是遭遇嘛。在前线20多岁死去,还是在养老院里面活到95,都是个人命运。
影片剧照
芭:这部戏里也是您首次启用专业演员吗?比如像马丽和章宇,跟他们工作和之前跟您的“御用”演员之间的合作有哪些区别或是否带给您有新的感受?
耿军:章宇和马丽到了鹤岗之后,他们的互动特别有意思。他们到那之后就特别想把自己融入到鹤岗这个小城市的环境里面,要跟我们当地的一些演员融为一体。这是他们专业演员主动要做的工作。而我的那些演员呢,想这两个人演戏挺厉害,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偷师。形成了这样的互动。
我的那些演员演了我这么多年电影,他们跟专业演员演对手戏的时候也不紧张,比如马丽跟小二演戏,马丽特别高兴,因为她看过我的电影。演戏之前她送给了小二一个兔毛的帽子,他在现场就戴着。他们其实在某一些层面来说都是那种比较单纯的人,没有跟我之前的经验差别巨大的东西。还是按我的方式拍,我的拍摄方式挺笨拙的,一个镜头拍好多条,拍几十条,就像男主角和诗人在儿童公园卖诗集的那场戏,拍了42条。还有的戏当天拍完之后,我们回去看回放,就觉得太好了,这没问题,而当大家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第二天再复拍,这种情况也挺多。大家配合度都特别高。大家看到剧本之后,觉得要拍一个好电影,需要一点时间,需要耐心,需要特别好的心态。
比如章宇去了剧组,智能手机都不用了,也不上微博了,也不玩朋友圈了。他每天非常自觉的在地里边溜达玩,也不化妆,其实就想脸色能有周围本地人的一个质感,小雀斑也都出来了。马丽也是一样,她其实在三十五六岁这个年龄段,在正剧里的表现对于熟悉她的观众来说,其实还挺新鲜的。这种表达,她也特别舒服。她自己中戏表演系毕业之后跟林兆华一起演话剧,后来因为演喜剧成为喜剧明星演员,她自己说我其实特别想演正剧,但找过来的还是喜剧多嘛。挺有意思的,每天我们那儿的纬度跟北欧一样嘛,下午3:30就黑天了,收拾到酒店4:30,吃完之后,再喝三顿酒,一回去一看晚上10:30。铁锅炖、鹤岗小串……拍摄期间也给当地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影片剧照
芭:拍摄持续多久?
耿军:拍摄是60天,两个月。前三个月美术组先采景、实景改造这些工作,剧组到了开始拍到杀青正好两个月的时间。
芭:天天喝吗?
耿军:回到房间就得喝点,因为外边太冷太冷了,我们最喜欢喝的就是60度的酒,管用,喝了身体就暖和了,有点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种酒鬼似的。40多度酒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酒兑水了那种感觉。我们那段时间喝最多的就是北大荒60,那玩意挺管事的。
芭:当时外面多少度?
耿军:零下20多度,在一刮风就已经很冷了。其实我是穿得很厚了,羽绒服外边是军大衣,棉鞋什么的都很厚,但是你出去走路没事,但在那场地一待半小时就透了。他们演员比我穿的还少,像刚哥他们在没演之前就已经就脸都冻紫了,我说赶紧跑步去吧。跑20分钟才能演。
芭:整个拍摄过程中也是很艰苦的吧?
耿军:我自己本身觉得不算艰苦,正常劳动嘛。拍电影的时候就是奋斗啊。大家其实唯一的困难可能就是温度吧,其他的没什么,冻够呛这事儿是常见的。
影片剧照
芭:可以聊聊这个关于“狠人”或者“狠”的这个定义吗?电影里边说坚强约等于狠,然后我们后来讨论的时候也说,您塑造的角色几乎都带着一种狠劲,当他们遇到事的时候,极少有歇斯底里的情况,都是闷声办狠事。
耿军:这里首先是人类动物性本能的那些东西。狠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动物面对危机最脆弱的时候,才会出凶相。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双重的含义。如果相安无事,谁犯狠呢?“狠”来自于虚弱,虚弱的时候人才会狠。我们在社会生活里边,能“狠”的机会是很少的,如果是懦弱的人,你就是一个软柿子,你就被人捏了。当人能用狠把被欺负和懦弱的东西克服掉的时候,那里边有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既是你最脆弱的一刻,同时又貌似是最勇敢的一刻,所以它具有特别双重的层次。
芭:电影里不管是徐东去也好,或者马丽发现丈夫“”也好,很多情节可能在其他地方人物会表现得歇斯底里,但是在《东北虎》里的表达反而是看起来非常平静。这里面所有人不管多大的仇,没有一个是那种用吼叫的方式去表达。
耿军:吼是惯性状态的失常,那种特别表象,我不喜欢那样的方式,我喜欢这种绵里藏针的,就互相猜闷的。这里边是那个有这种真正的心理较量的。
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就是内心戏的那一部分是最难演的。我们在拍马丽(饰演的角色)见郭月(饰演的角色)那场戏,男主角徐东也在,大家在饭店里,那场戏演员消耗太大了,章宇说:“哥我就在这坐着,我觉得比那个吊威亚一顿奔跑比那些都要累。”你只有在恐惧的时候才会全神贯注。那种随时不知道有一只什么样的箭,朝你射来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这个危险来自于哪个方向,是来自于他老婆,还是来自于他的情人,还是来自于眼前这瓶酒。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太可怕了,相当于就生生的就逼到了一个墙角。
再比如,吃蛋糕那场戏,章宇有一句台词是“好的”,我们在拍这场戏的时候,他说导演这个“‘好的’,我是不是可以不说?”我想了想说,不行,这个“好的”是什么意思?是我服了,我求求你了。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事,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可能你完蛋了,你招吧,那就坦白吧。所以男人还是很弱小的,又弱小又脆弱。当然它也是因果关系,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主观积累的。
影片剧照
芭:发生在徐东身上这么多故事性的情节出现,与以往的您对男主角的设定相比,更具有故事性,更多情节和冲突,可以说是您希望让大众更容易进入场景的一种尝试吗?
耿军:创作剧本的时候我没有考虑这些事儿,这完完全全是个人审美、能力和个人趣味点的走向。这个是我的趣味,进行这样的描述是我的乐趣。我觉得先解决我觉得有意思这件事,这个是我要干的事儿,得我觉得有意思。比如情感戏,“”出现这种戏,怎么写?它出不出现?它出现了怎么办?那酒她喝不喝?在我们写剧本的时候,这种场面怎么写最难写,我们就怎么写,这种这场面怎么面对最难,我们就怎么面对,是用这样的方式写的。其实是主要还是创作的乐趣和写作的、感受上的东西。当我写到徐东情人拿着口杯子干了一杯,“我祝你们一家三口快乐。”她就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写到了。
芭:跟过去拍您的其他的影片相比,您在拍摄、对于电影的观念跟表达手法上有哪些发展和变化吗?
耿军:这第一阶段就是拍《烧烤》、拍《青年》,还有这些短片,这个阶段可能是有点接近于画画里边那个素描、写实。再后来《轻松加愉快》,到现在的《东北虎》,是在原先的基础上,我管自己的第二段创作叫“荒诞现实主义”。个人在创作上想有一点变化,突破是件很难的事嘛,这种东西是自找的,就是自己向往的,能不能做点变化?能不能每次拍的东西都跟这些演员的年华靠的近一点。我以前在拍电影的时候,我跟我家乡的演员说,我说我们的生活太平淡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可能唯一有的变化就是人去世了。我得要用电影来把大家的人生再写一遍。我在我那几部电影里边,张志勇就叫张志勇,徐刚就是徐刚,我说你们自己的人生,加上电影里边的,你们就相当于有两种人生。你去剧组拍电影的时候,就去演每一个不同角色的时候都会有新的人生。他们不到30岁的时候演这个,过了30时候演这个,40的时候演这个。如果大家还能一起玩耍得比较好的话,可能演到50来岁、60、70岁,我觉得就像弗朗索瓦·特吕弗和他的演员,从400击一直拍,从少年、结婚、生孩子、40来岁。我觉得那个挺好玩的,其实是跟电影一起生活,电影人生。
《东北虎》导演,耿军
2020年4月份徐刚的父亲去世了,在我们那里,家里边父亲去世的遗体,儿子是不抬的,是殡仪馆工作人员和儿子的哥们从楼上往下抬。他父亲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演了我的电影叫《青年》,我们从5楼往下抬他的遗体,我心里边想我的一个演员去世了。我们家里边鹤岗本地的生活,和我在北京的生活,各有各的那个环境啊。但是平庸这件事是没有人怀疑的,太平庸太苍白了。需要搞点创作才能打发看不惯的人生嘛。我特别看不惯的人生,我要用创作来打发掉、来填平。创作是跟平庸生活的对抗,是对抗平庸生活的手段。还好,我们两三年拍一个,我们这样持续地对抗平庸。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每天都在对抗平庸,因为我要写作嘛,还要写剧本,他们只有演的时候才有机会对抗平庸。所以我可能比他们没有那么平庸。但是我也痛恨平庸。
芭:在您的影片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戏剧感,那个场景非常真实,但同时又感觉很像一个舞台搭的景。人物对白之间也会有一些同日常对话不一样的节奏,我们总有感觉,这些人话里有话,都像有很多潜台词没有说出来。您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您的影片?
耿军:随着那个文学修养逐步提高,我自己写剧本到拍摄的时候,那个时间特别慢长,当剧本固定了,演员开始读剧本,到拍摄现场,我剧本里边的台词是改不动的。你想过来现场改我的台词,你能拿出来更好的行,拿不出更好你是改不动的。有的台词,是第一稿剧本写了出来后就没再动,还有的是反复修改出来的。像我在写就比如说你刚才举例子“坚强约等于狠”这句词,那这个东西是惯性思维里来的吗?不是。是在那一刻的时候,角色本身创造了这句话。那这句话应该是我们现在这个语速吗?不是。如果我用心跟你说话,我语速没有那么快,我要把人跟人在这个场面里边的那种张力给表现出来,是你来一句,我往一句,是需要思考和等待的空间的,而不是那种我们生活里边说的没有质量的话。我们在戏里边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心在说话,虽然我们是敌人,虽然我们是对手,但是我们也是用心在沟通。我要弄“死”你这个心是有的,我不能让他弄“死”这个心引导出了我得想办法,比如约到派出所门前谈这个事儿。所以这些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第一次面对对方这个个体,因此他们每句话都是有一点思考空间的,我把那个物理时间留了出来。
《东北虎》导演,耿军
芭:电影这个事儿为什么令您如此着迷,而不是去搞其他的创作,比如说您为什么不写小说或者做其他形式的创作?
耿军:就是人得活得有点意思,得有事干,干什么都行。我在家乡的时候喜欢泡图书馆,看小说,我们一开始看的都是大部头,《白鹿原》《悲惨世界》这样的,让我当作家那太难了。我要是从小部头看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这玩意我也能写,我们从大部头看的时候一上去标杆就给立住了。后来我在图书馆里边发现了刘恒的剧本集叫《》,它里边有《本命年》《》《大红灯笼高高挂》、路遥的《人生》,我看了觉得剧本我倒是可以写,我可能能做个编剧。我就试着写一写,就跟买药似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三个疗程。只要这事开始干了,我就开始琢磨这事了,就开始就连根拔起,比如我喜欢贾樟柯导演,就从他的访谈里面就找到了贾樟柯导演喜欢谁,他喜欢《骑自行车的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那帮人又喜欢罗西里尼……他们盘根错节,这些东西其实就变成了巨大的兴趣点,变成一个宝藏,我就想,我去挖宝藏,不也得给宝藏留点东西嘛。能把作品做好,可能就是不单挖了宝藏,还能给宝藏里边放点宝藏。人嘛,出来混就是要还的嘛。
芭:我们看到电影里每一帧的画面构图、光影色调都非常讲究,您也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吗?
耿军:电影是一个综合创作,我身边很多人都是画画的,我弟弟就是美术班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搞美术的、画画的,还有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人,后来他们转行去做装修、园林设计。电影嘛,摄影师、美术师和导演是负责视觉呈现,一个镜头摆在哪、演员穿什么,屋子里边是怎么陈设,这些东西都是电影功课,把它给在合理的范围内视觉上能呈现的好一点。说一个电影太好看了,每一帧都是油画,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尽量在靠近、在做到的路上。
影片剧照
芭:可以聊聊电影中关于梯子的意象吗?比如派出所的警察修理路灯上的监控器,其实也可以不登梯子,但还是特地弄了一个梯子的道具;第二个出现梯子的地方,就是小二的那个梯子。
耿军:一个是体制内的梯子,一个是体制外的梯子。在电影里,小二一共两个重要道具,一个道具是风筝,是往高了飞的;一个是梯子,他以前在建筑工地工作,现在建筑工地不景气了,把家里边的东西拿出来卖一卖,恰巧女主角路过的那一刻他卖的是梯子。就是这两样东西,都承载了我个人愿望,我希望困在这儿的人能登高看一看,别真的就困在这儿,有的时候那个风筝就飞在天上,我希望大家能走出被困的那个地方。哪困你了,你就走从哪走出来。
撰文 | 黃金狗
编辑 | 荷大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