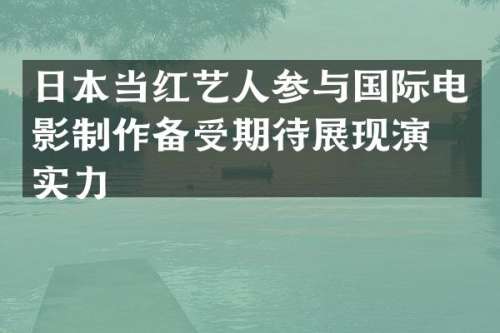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新作,贾樟柯监制,蒂尔达·斯文顿主演的《记忆》近日获评法国《电影手册》年度十佳第3位,本片此前已获第74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并将代表哥伦比亚竞逐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电影手册》近期也刊载了对阿彼察邦的新专访,导筒本期带来本文翻译,走进阿彼察邦远离泰国奔赴南美后的影像新途。
《电影手册》2021年11月刊
阿彼察邦执导,贾樟柯担任制片的《记忆》女主蒂尔达·斯文顿登上封面
法国电影杂志《电影手册》公布2021年度十佳影片:
发生在体内的爆炸
——《电影手册》访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译者: 火鲁斯特
从《幻梦墓园》到《记忆》已经过去了六年,这段时间您都做了什么?
阿彼察邦:我没有闲着。那时我对泰国所处的局势以及它即将面临的未来感到非常不安: 军队在拍摄《幻梦墓园》期间无处不在,它掌控了整个国家。同时我办了几场展览,也在为《记忆》做筹备。(泰国军政府审查没有“杀死”的阿彼察邦)
为什么选择在哥伦比亚拍摄?
阿彼察邦:2017年,我被邀请到卡塔赫纳的海文学节参加回顾展, 当看到由我所有的作品节选集合成的预告片时,我深受感动。我把它当作一场葬礼,并在那时意识到,得重新做一些事情,开启全新的生活了。之后的三个月内我去了很多次哥伦比亚的艺术家驻地。那里,我被当地的建筑,被人,被一些充满活力的、不稳定的东西所吸引。我受到启发并开始写作。《记忆》来源于个人的观察,是我在那样确切的时刻所发现的。
看来无论拍哥伦比亚还是泰国,您都同样熟悉。
阿彼察邦:是的。开始我以为《记忆》将会有别于我的其他电影; 但是,在观看样片时我逐渐意识到在节奏、运动和灯光方面它们有多么相似。我觉得《记忆》这个故事超越了某个特定国家的地理限制,它可以同时发生在哥伦比亚和泰国,也可以发生在其他地方……也许就在这里。
您是如何和西班牙语打交道的?
阿彼察邦:我并不明白演员之间在说什么,但是除了与语言老师合作之外,有些东西即使不懂这门语言你也能感受得到: 那就是表演的准确性与节奏感。我不想在剪辑过程中,因为我非常重视一镜之内的转换和部署,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在必要时多次重拍,以达到语言方面的准确性。
第一次和像Tilda Swinton、Jeanne Balibar或 Daniel Giménez Gacho这样的专业演员合作,有没有使您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
阿彼察邦:我们的工作过程和我在泰国拍摄电影时别无二致。但我花了较多时间去把握人物,特别是Jessica ( Tilda Swinton ), 因为这个角色的维度更加虚幻。或许也因为在她身上有很多我自己的影子。相反,在之前的影片中,像Jenjira Pongpas 或 Sakda Kaewbuadee,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演员,演的都是和他们本身非常相近的角色, 我努力让他们忽视摄影机并做回自己。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记忆》里的专业演员完全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Jeanne是那样特别,她有一套充满复杂性的动作,有时看上去很超现实。Tilda有某种更透明、更动人心弦的东西,需要经过调整才能使她成为真正的Jessica。她给了我许多选择,看到这个人物的演变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
《记忆》片场
在叙事中,哪部分是已经写好的,哪些又是即兴发挥?
阿彼察邦:对我来说剧本只是一个基础,当着手去进行不同的尝试时一切才真正开始。得承认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去往哪里。我们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拍摄,我也花了些时间去理解这部电影。用35毫米胶片拍摄五至十分钟的镜头,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专注度。这如同一场仪式。
梦在您的电影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您会把自己的梦融入到创作当中吗?
阿彼察邦:会,很经常。我们的生活由两种不同的的叙述形式构成,且这两种形式永远不会重合: 那就是有意识的经验和梦境。电影,是二者的混合。
电影《记忆》开始时出现了一种声音。关于它的起源,能不能再和我们多说一些?
阿彼察邦:在开展这个项目几年前的某天,我听到了一声类似爆炸的巨响。起初我以为声音从外面传来,后来才发现它源自于我的脑海。从那之后这种声音经常出现,尤其在清晨。几个月来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直到上网搜索才了解到我可能患有所谓的“ 爆炸头综合症”。就好像你的颅骨是金属做的, 而有人在里面弹橡皮筋。这种声音让你完全处在一个无意识的状态里。我学会控制它们的出现,甚至还从中找到了乐趣,因为它们允许我以一种新的方式倾听城市的声音。有时我看到声音以几何的形态出现: 方形、圆形,或闪光。自从拍了这部电影之后,就再也听不到它了。
赋予它形态(指声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吗?
阿彼察邦:混音室里的一组镜头非常接近我和音效设计师 Akritchalerm Kalayanamir ( 从《热带疾病》开始就和阿彼察邦一起工作) 的体验:我经常听见脑袋里的金属声,可就是无法准确地描述它,无法将它重现。最后,事实证明想要将它复刻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声音,更是一种声音的理念,一种内部的声音,就像一个人对着自己说话。拍摄之前我们准备了这个声音的最初版本,可真正赋予它形态是在后期制作的时候。我们在声音库中听过很多效果,敲打声、树木倒下的声音、蔬菜被切开的声音等。这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剧本,一个在电影制作过程中被再度创作的故事。
您怎样看待影片的整体音效与该声音的关系?
阿彼察邦:这部电影有它非常音乐性的一面。我觉得需要一种简单的音效从而使人达到冥想的状态。对于Jessica来说,同样也对于我,在哥伦比亚意味着失去一部分自我认同后,伴随着内心的空虚感,继而寻找一条全新的道路。聆听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事物足以将这种空虚感填平。
从技术方面看,这项关于声音的工作,对您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吗?
阿彼察邦:这是我第一次和音响师工作, 他是和 Carlos Reygadas 合作了很多次的 Raúl Locatelli。和他一起,我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特别是在声音的强度上。这是一种不那么纪实的方法,有更多的断裂、对位法,特别是在对话和沉默之间。
在影片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 街上传来了爆炸声,我们不知道这是Jessica听见的声响还是爆炸的声音,结果只是一辆公交车的发动机出现了故障。在这期间,我们注意到一名男子好像受到惊吓似地跑开了。
阿彼察邦:这源于我在波哥大真实的观察。在哥伦比亚遭受恐袭的时期,城市里的居民无时无刻不在感知巨大的声响。《记忆》讲述了这种触碰与暴力有关的某物的幻觉,它在电影中被重现,同时也存在于哥伦比亚的历史当中。你完全可以真正书写一个 “嘭!”的故事,它关乎于哥伦比亚人的历史与记忆,从庆典的声到谋杀案的声,以及所有被媒体报道出来的暴力事件。因此这种声音可以被当作一种对暴力的模糊回忆,如同一道伤疤。
雅克·图尔尼尔的《豹族》中也有类似的桥段:在某个特定时刻, 你以为听到了豹子的叫声,实际上那只是一辆公交车。
阿彼察邦:这太疯狂了!我都不记得了,虽然雅克·图尔尼尔的电影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在《记忆》中, Tilda Swinton 扮演的角色叫 Jessica Holland,就像《与僵尸同行》里的僵尸女人。我想让我的人物像她一样,在最后成为某种形式的傀儡。在图尔尼尔的电影中,她也被伏都鼓这种黑人音乐的声音所催眠,尽管她是一个白人。并且它同样通过对土著文化的诠释使殖民化的余温涌现。我觉得我的Jessica,正如图尔尼尔的Jessica,并不真正存在:她有着超现实的一面,不能在电影以外的地方存在。她如同微型计算机,收集声音、色彩。她就像一条波段,并试图与另一条波段同步。她就是电影本身。您知道的,《 记忆》是一部遵从线性叙事的电影。我觉得它像日本俳句:嘭!… 走,走,走,走。这样。
电影里出现了很多 “洞”, 头骨上 、地板上、天空里….
阿彼察邦:是的。这与另一个主题相连 : 圆、环形。这些洞仿佛土地、时间、记忆被击打留下的印记。再次回到我对那个声音的感觉,它像某物的击打一样不断在我体内出现。并且它也与波哥大几何风格饿建筑存在关联,这些建筑有着令人惊奇的弧线。
您觉得两个Hernán是同一个人吗?
阿彼察邦:两人如同双生子并且都和声音相关联:第一个在混音室给了Jessica 她想要的声音,他代表了人工创造,一种人类的发明。第二个人以有机的方式传递声音,他将生命、记忆的音乐具象化。
最后在森林里起飞的,是一艘飞船吗?
阿彼察邦:我并不总准确地知道我所做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在最后一部分所发生的,象征着一种在时间中沉睡的集体记忆。我将它与儿时的记忆、对森林的感知、以及我对科幻小说的兴趣相混合。这部电影在某种极其古老的东西和对未来的愿景之间延伸。它可以有很多解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达到一个点,让观众可以接受一切,而声音使这种开放性变得可能。当飞船降临,这虽然难以置信,可我想他们还是接受了。我希望使一切简洁明了,有点像是七十年代科幻小说的封面!
《记忆》片场
所以您很喜欢科幻小说?
阿彼察邦:对。我被不计其数的科幻小说和电影所影响。就比如我非常喜欢电影 《逃离地下天堂》( 迈克尔·安德森,1974 ), 一个令人不安的反乌托邦故事,它讲为了避免人口过剩,人类被设定年轻时就死去。
您是否和图尔尼尔一样,也真的相信平行世界的存在以及有死者活在我们中间?
阿彼察邦:我相信万事万物都彼此相连的泛灵论和佛教环境中受到的教育。比起相信或不相信,不如说它以不可磨灭的方式标记了我。
然而我与此同时也被浸泡在科学的氛围里,因为我的父母是医生。我在医学书籍中长大,我想电影也与此有很大关系,在《与僵尸同行》中这种对身体、对有机生命、对自我的关注尤为明显。
您目前在筹备下一步电影吗?
阿彼察邦:是的。这会是一部非常长的电影,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其中南美洲将占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仍会是一个关于健康以及自我的故事。这次,我不会再说它和我其他作品不同,因为我曾以为《记忆》是这样,但其实不是。
采访由Claire Allouche和Marcos Uzal于七月五日在巴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