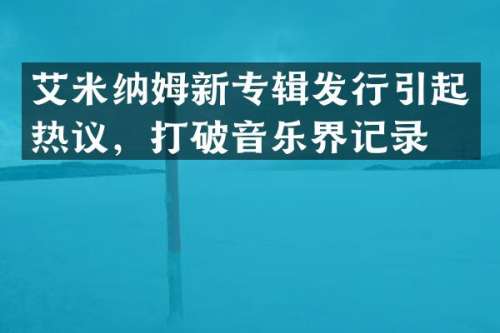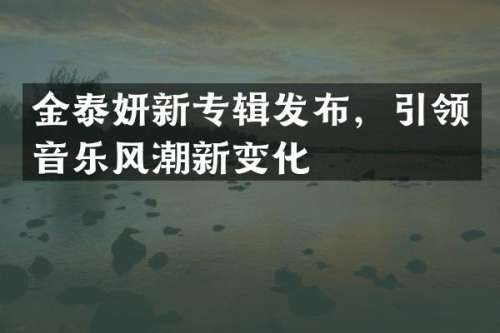布鲁斯·亨德里克斯:要想讲好故事要有好的想法,在电影当中,编剧将一个想法做成剧本,可能我们今天最开始先来谈一谈从编剧角度的想法,(英语)也是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人,赢得了5个电影奥斯卡奖,珍珠港先从您来谈?你们在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最开始要做什么?
兰道尔·华莱士:我确实总给人带来惊喜,但是我一般写剧本,之前我都要做精细的调研,因为你要知道故事背后发生的原因,才能够知道这个故事的原因怎么发生的,在我职业生涯当中最棒的一部分,当时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可能要结束了,当时我在想如果有一个机会写东西我会做什么,当时我跪在地上起到,当时只有一次机会在写一些东西,我可能并不一定写好莱坞买的东西,我可能会写一些我的子女愿意去看的东西,我会写一些心潮澎湃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重点在,确实写故事要有,因为我觉得其他人要想做到这一点也是一样,我们坐到这里我们听到很多比如说贝多芬的一些精彩的音乐,有可能就会心潮澎湃,我们作为美国人能够听到如此美妙中国的一些声音,听到他来唱贝多芬的欢乐颂这是几百年前写的,我们感受到那种激动,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英语),他是一个英国的精神,不要说我们的头是不是在一起,而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在一起,我也是找到一些方式,把心理的故事的情感表达出来。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董先生你觉得你在写《老炮儿》人物的时候,你的灵感来自什么地方?
董润年:我们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还不是完全的了解我们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得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现实中去采访,去观察,然后写的过程中会把原始的素材能够慢慢的结合起来,把它变成一个能够成立有价值的人物,通常写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你之前预想的很多东西其实不对的,你以为这个人物是这样的,但是那个人物会慢慢的形成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会有他自己行动的逻辑。如果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编剧需要顺从你的人物看看他到底做什么,如果强行让他服从你的某种抑制的话,这个东西一般会失败,根本写不下去。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那我想问一下陆川先生,您在选一个故事的时候是有什么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是他的主题还是人物、情节?
陆川:首先我想说,我是《勇敢的心》这部篇的影迷,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见到您,非常感谢!我想可能是人物吧,人物的命运对我吸引力最大。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那在您写编剧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发现的过程吗?
陆川: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写剧本或者拍戏的过程非常像一个旅程,逐渐触摸这个事件的核心,了解剧中人内心的秘密,很像是一个发现的旅程。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那么贝蒂·托马斯你是一个导演,你现在也是一个监制从作者的角度,制片人的角度,他们可能需要对他进行一些改变,你作为一个导演怎么去组织这样一个过程,以便能够把重点突出出来?
贝蒂·托马斯:通常我说话是这样的,有没有说好的演员不需要拿话筒的,但是今天我还是拿一个话筒讲吧。大家好,好完全,当然每一个剧本都不一样,我也会做喜剧,喜剧重写改变,通常是要一群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怎么说呢?所有一切都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就像我们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而我们需要有一个人作为主导的人,他会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那我是希望作为导演作为那样一个人物存在,有的时候我不能够做,但是你得让人们关注你所做的电影,而不是他们做的电影,如果每个人七嘴八舌肯定达不成你的目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演员都会给你一些想法。所以我作为导演必须作为这样一个人,我会说这就是电影的内容,而不是你想要他成为的内容,这就是电影的内容。然后我也许会逐渐的发现说这个电影到底是什么。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问我们中国电影专家导演,中国电影非常成功,那么这个成功有没有把你们想说的故事说出来呢?
安晓芬:我是一个制片人,我跟前面几位都不太一样,他们都是创作者,而我应该说是电影产业的影音者,我基本上其实在制作一个电影的时候我会首先从市场的角度处罚,我会衡量观众喜欢不喜欢这个题材。如果我自己和我的同事都很喜欢的话,那么我们在去看题材和剧本是不是符合要求,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然后这两点都确认了我们才会开始制作一个电影。经过寻找到好的主创、编剧、演员,把这一部电影打造出来推向市场,让观众检验喜欢不喜欢,观众的喜欢和我们的判断是不是一致的。这个是我做一部电影最初的一个过程。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问一下我们的编剧,当你们写剧本的时候,你是一直想它的结构吗?转折点在哪儿,往什么方向走?
兰道尔·华莱士:我是到后来才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写作其实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纪律,是一种灵感的结合,所以我觉得首先是灵感第一,我以前一个导师告诉我,要想去把这样一个电影的剧本写好,需要很多这种灵感的,所以我首先想的能够把我这种,把我的灵感把我的这种心中愉悦激动、痛苦、悲伤所有倾向出来的东西倾泄到纸面上,然后再用我们这样的艺术,技术的手段再来进行改变,这个故事怎么样架构会更好,我非常喜欢您刚才说的,这个里面的人物在跟你对话,有的时候这个人物开始说出一些我自己说不出来的话,甚至想不到的话,所以这个剧本就活了,如果到这样一种程度的时候,就开始要将我的一些艺术层面的东西放进去,比如说这个故事从哪里开始,你知道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一些艺术的原则,这些还是有用的,但是我经常也会说我不知道说,如果不知道一个故事怎么结束,你是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简奥斯丁著名作家曾经说过,如果这个故事不能够让协作者吃惊也不会让读者吃惊。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导演能够让全球的人看到你的电影,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重要对你来说?
康洪雷: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方向,讲好一个故事,能让全球人都为你喝采,当然也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们也在努力着。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那中国的观众跟美国观众挺像的,他们也会喜欢那种科幻、玄幻功夫片、喜剧片,那么在中国是不是从历史剧转向这样一些剧,还是说市场扩大了?
董润年:编剧可能有的也说不太清楚,能不能说一下刚才那个思考结构的问题。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当然可以。
董润年:关于结构的问题我们当初在学校里面学习怎么写剧本的时候,曾经写过很多关于怎么构架一个故事,包括美国方面的制作教科书,写作的时候发现不能够以教科书里面教你的东西去告诉你怎么讲这个故事,故事肯定是原发的,你到底想怎么样讲这个故事才成立?而且我现在慢慢的在尝试一种东西,包括之前跟宁浩导演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在设想三部剧,好莱坞经典的这种,其实不是好莱坞,是西方经典事实结构,是不是完全适合中国的,因为我们觉得中国的观众还有中国人在表达情感和感受这种情绪的时候,跟美国的观众和美国的角色不一定一样,中国人可能更含蓄一点。有的时候发现在美国电影里面或者美国电视剧里面,通过很简单的一场戏,演员一两句台词就能够把某种情绪逆转过来,但是在中国戏剧里面很难做到,因为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特别直白热烈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之前在制作过程中经常带来一些困扰,按理说经典的三部剧的叙事结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扭转这个局面了,实际具体写作过程当中扭转不了,不是特别可信,可能我们在尝试。可能中国传统叙事的文本中有一种说法,叫起程转合,这是一个四幕剧的结构,实际把好莱坞第二幕拆开了,在第二幕和第三幕增加了一个故事的转折,要单独形成一幕,这个我们一直在尝试考虑说,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电影叙事过程中要跟这种传统的或者经典的西方的叙事模式有所区别,这是我在考虑尝试的一件事儿。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电影是朴实性的,我跟陆先生也谈到他的电影,《可可西里》,我也是特别喜欢看中国电影,我看过很多中国电影,我觉得这种情感是朴实性的,陆先生能不能谈一谈你选择的这个电影的结尾?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像是一个经典电影的西部片,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如果是一个好莱坞电影的话,英雄赢了走向日落,但是这里是坏人赢了走向夕阳,让我感到吃惊,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而且总是在想这个电影。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有冲突,还是你一直做这样一个结尾呢?
陆川:其实我把结尾改了,在原来剧本里面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这个脚本,而这个电影像西部片,他们喜欢这个结尾,因为在最后队长打败了偷猎的人,很好,它是一个商业片。但是为什么我要改呢?因为我觉得有个感觉,当我到了那个地区之后,我觉得人是很脆弱渺小的,我们无法打败自然。我觉得我不能够说谎,所以我改了,把结尾改了,几乎我失业了改这个结尾,所以索宁、哥伦比亚他们对这个结尾进行测试,行吧,就这样做,我在这个电影当中扮演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现在对一个导演来说那样一个决定不太容易,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文经常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制片人可能不喜欢,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矛盾,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你聆听自己的心,你也要遵循这个行业的行规,这没有答案,但是在电影当中我还是选择了要说出真相。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非常好的选择,导演可能就是要做出有一些创意的选择,作为一个导演在剪辑室里你也有这样一个选择,你觉得有时候有没有困境呢?每一幕每一个情节都要符合人物的,在剪辑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有些时候必须把一个场景保留下来,或者不保留,可能你拍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么多呢?
贝蒂·托马斯: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我是说你内心是不是有冲突有挣扎?
贝蒂·托马斯:没有挣扎,把他扼杀在萌芽当中,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那个最喜欢的一个,比如说小场景很漂亮,很精彩,然后一切都很完美,那孩子们,大人们都喜欢,可是他对你的情节没有意义,他对你这个电影流动没有意义,那就杀在萌芽中地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问一下你们在合作当中的合作伙伴吧,就是你们的演员,作为一个得奖的演员?描述一下你们的关系,你们一定对这个过程还有这种跟演员的关系有独特的看法,你们是不是说很早就让这个电影参与到写作剧本的过程当中?
贝蒂·托马斯:没有,如果说我离他们远一点就远一点,有的时候不行,离不了那么远,他们会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不一样,(英语)是另外一个人,他们都不一样。那有些人他是希望全程参与到这个剧本写作,有的人不愿意参与的,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演员他们来成为一个导演参与这个写作有没有好处,不太确定,因为演员他们是很脆弱的,他们也凭自己的直觉行动,所以根据他们的直觉做事情,有的时候直觉是好的,有的时候这个演员说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种问题或者说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改变我刚才拍的一个场景。所以他说你犯了错误怎么把镜头放在那儿,他们会有很多意见,然后可能你放在那儿看不见另外一个讲话女孩的脸,所以他们的东西不可信的,这种时候有时候没有帮助的。
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帮助吧。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你是怎么跟演员合作的呢?是不是要跟他们演练很多遍?
兰道尔·华莱士:我不让他们提前演,我在拍《勇敢的心》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拍摄过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思考这个故事思考了很久很久,然后当时我的妻子怀孕之后,生了第一个儿子,后来探讨这个故事,当时觉得整个故事由我内心思考出来的,当时我的父亲、妹妹都读了这个故事,他们其实从心底感受到这个故事的力量。我记得父亲甚至跟我说甚至能够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哭泣的肩膀,所以这也是证明了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作为一个编剧能写到这个陈度,如果能和其他导演导这个剧我也非常荣幸。因为整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和谁合作我处于主导地位,因为编剧负责写,演员负责演,导演负责导这是正常的状况。但是我写的这个东西,我基本上全心全意写这个东西,甚至写的这些东西很多是我自己。所以我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写这个东西的,这个导演接下这样一个电影也是很有勇气的。当我在导演的时候,我并不会给他们一些具体的指示,会让演员本色的来演一下,然后我再去看,像养孩子一样不能告诉他们做什么,不断更正他们,应该给他们机会玩耍,之后塑造整个的电影。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你觉得导演当中最难的是什么?导演过程当中你最享受的是什么?
康洪雷:难过就使前期的准备,特别跟剧本,因为现在很多导演我们在前期介入到剧本当中去,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称之为,在监狱里面,当这个剧本最后完成之后,大家都认可以后,那一天的晚上我是睡的最好的时候,我认为出狱了。最愉快就在拍摄当中,那时候最愉快的时候,整个拍摄的现场你和演员创员在一块,你天马行空,你可以时而是胆小如鼠,时而是气壮如牛,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创意,甚至你很多很多的灵感,那个时候是最最幸福的时候。
其次就是后期剪接,后期剪接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制约,你想这样做,有的时候投资人会从各种角度市场考虑希望你这样做,有时候取得的因素在里头,所以你经常会不愉快。经常会停下来,经常会想一想再进行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导演的三部曲,我认为中间这一部是最愉快的,谢谢!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陆导,您最痛苦的是什么?
陆川:我觉得也是编剧阶段最累的,因为之前几部戏我自己写剧本更累,自己写剧本最大的问题没有一个参照,你自己就能做所有决定,其实我后来发现像有董老师特别优秀的编剧出现之后,希望能够从下一步戏,今年开始能够跟职业的高水平的非常有才华的编剧一块合作,因为参照系有两个,大家能够互相批评校正,一个写一个导那种感觉非常疯狂,脚底下有一千条道,基本上没有一条道你知道答案的,那个状态是非常的分裂,基本上是在一个非常疯狂的状态下,也是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我也很同意康导另外一个说法,拍摄是最幸福的,刚才他已经描述了那种幸福,对我来说还有特别原因,拍摄期间吃饭就会吃的比较正常,每天都会有人送饭,早中晚,一般拍戏就变得非常胖,从一个不正常生活变得非常规律的,每天吃三顿饭,甚至四顿饭,加班还有宵夜这种生活,我觉得在剧组的生活很舒服。
康洪雷:所以根据导演的说法,编剧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他们还有舒服和开心的,所以我们永远在监狱里。所以我经常把编剧请到现场去,去看去了解,其实挺好的,有的编剧到现场去多走一走,挺好的我认为是。
陆川:新的中国电影的一个趋势是大量的编剧都离开了编剧的岗位变成了导演。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确实这是挺常见的趋势的,董先生您遇到过的比如说和导演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完全写不下去,必须要放弃的时候?
董润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顺从的编剧,我会尽量去理解导演他到底在这个过程中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还是认为剧本不是小说,不是一个完全的完成品,因为他需要别人,就像刚才那个问题需要重写,其实导演重写,演员也是在重写这个剧本,你可能会发现你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当你遇到一个好的演员的时候,你之前写的时候,你脑子里想象的场景也许没有这么生动,但是他给你重写就会变得更好,你得相信他们,相信导演,相信演员甚至相信观众,我觉得观众在最后也会重写你这个剧本,他会解读出你在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想说的其实作为编剧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相信导演,相信你合作的对象。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你做导演的时候你得到的最好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贝蒂·托马斯:我觉得是要做到全面,李安曾经跟我说过,你要走出去,去吃好吃的,就像拍摄一样,享受美食一样,然后买好原材料做出来这就是剪辑。但是你不要忘记,有的时候可能原材料市场关门,你可能只能买一些非常便宜或者吃到快餐,或者非常一般的东西。但是你要保证在拍摄过程当中,你要有非常出彩的那些食物,所以尽管你可能原材料没有那么好,但是你仍然可以用不是很新鲜,不是特别好的原材料做出好菜,这才是最重要的,整个这个过程最好的建议就是导演有像买菜做饭一样。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作为一个导演,你在拍电影的时候,是否会想到后期的工作呢?你是否拍的时候想到后期,从而改变你拍摄的方式?
兰道尔·华莱士:在每个阶段大家面临的压力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局面我控制不了,我觉得剪辑的这一部分,实际上(英语)曾经说他非常喜欢后面剪辑这一部分的,我还年轻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17岁,当时看了一个电影是(英语)的电影,我是自己看的那个电影,走出电影院之后跟我自己说,我因为看了这个电影我的人生因此有可能而不同,如果我以后做电影我是想做出这样的电影,因为人生太短了,你必须要做出那些能够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东西。(英语)他曾经说过,电影当中其实最重要几个重要的时刻,对于我来说做创造当中找出高光的时刻,如果我看到以前我没见到的东西,看到了一些比如感到惊讶,感到有的东西我会牢牢记住。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中国,这时候第二次来到中国我记得中国的一些谈到中国未来的发展。然后其实甚至也回过国,世界最伟大相爱的探索家并没有中国人,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太对的,所以我想很多时候你要做到既要去算计又不算计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很困难但是可以做的到的,因为我觉得做电影过程当中其实就找到最神奇的那个时刻,但是我觉得您确实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我想在和人生相比,其实还有很多比人生更重要,更超出人生的一些东西。因为你可以相信这一点,这样的话你可能在你迷失的时候才能找到真的意想不到的东西。所以你无法入眠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想到比人生更重要,超越人生的事情的话,并且艰辛这一点,人生当中可能有爱,有喜悦、信仰等等这些东西会帮助你很多。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陆导?想问一下您第一个在做的英语的电影,讲故事是关于讲故事,你觉得做英文电影和做中文电影有什么差别呢?
陆川:整个过程完全不一样,比如我做导演生涯中间第一个没有完全剪辑全的一个电影,所以我特别不习惯,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剪辑师他们去剪片子,每次剪完之后让我看提意见。那么在中国导演和剪辑的关系基本导演是(英语),剪辑师坐在剪辑抬上,导演就坐在剪辑设备后面,导演100%控制剪辑,但是在英国这是不礼貌的,你一般情况下就是他剪一半让你提意见,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不同。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因为在我们剧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英国人,制片人是美国人,我就带了一个助理过去,所以很多工作习惯都是不太相同的,最终我很感谢迪斯尼的制片人(英语),他还是让我把电影带到了中国重新剪了一遍,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北京剪一部分片子,能够彻底表达我对电影的一个愿望,但是这次的合作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让我看到英国团队敬业精神,还有他们对电影的一个理解,因为他们来自于纪录片领域的,而这个电影是一个(英文)不是完全的纪录片,是一个故事片。我看到一个职业制片人的工作,迪斯尼制片人是德国奥斯卡奖的,他在如何讲故事,如何去组织艺术生产上让我学到太多的东西,然后他把中方的团队和英方团队这种配合,还有时间的安排都做的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故事其实又是关于中国的。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面,英国一共5个摄影师我们分成5个组在中国荒郊野外拍摄了18个月,我看到了世界最顶级自然摄影师他们工作的方式,让我非常震惊的。我们老说中国电影人非常会吃苦,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不会有这样的摄影师会花十八个月连续在野外拍摄,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而且他们的收入也非常少,并不多。
其实中国现在整个制作预算也在上海,电影收入非常增加,其实我们说电影预算的时候,英国很多商业电影包括艺术片电影都比中国的电影便宜很多了。所以中国其实我能感受到中国电影人既面临很好的机遇,也面临全球优秀艺术家的挑战。比如说我在拍电影时候在想,有可能我会用英国的摄影师,他们首先很专业,其次可能还比中国的便宜,而且做的不错。而且他们拍摄的语言可能是一个国际化的语言,其实随着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各个国家的艺术家,来到中国去为中国的题材拍电影,这可能也是未来一个趋势,也许未来北京就像洛杉矶一样,作为一个电影的中心,但是街道上走着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可能是一个未来。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安女士您作为一个制片人提一个问题,最近也有一些美国的像《变形金刚》这样一些片,也是塑造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形象,并且甚至还有一些人把中国的故事带上全球,您作为一个制片人,您觉得中国的这些故事,以后是否能够会有一些比如说英语或者其他语言的人演,会把他们带到国外吗?有这样趋势吗?
安晓芬:我觉得中国电影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努力,特别希望中国电影能够走出去,让全世界的观众了解中国,但可惜的是能够走出去的电影特别少,应该说只有张艺谋的《英雄》当年走出去过,在全球获得过不错的票房。剩下几年尤其近几年可能我们的对外这样的成绩特别不好,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跟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电影创造者,还没有找到跟全球的观众,这种对话的形式,表达形式,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让他们能够接受,这是需要我们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当然如果走不出去的话,我们可以请进来,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那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国际合作,包括好莱坞的电影工作者,还有像欧洲很多国家的电影工作者也到中国来洽谈合作,我觉得可能会在电影人和讲故事的方法上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诠释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我相信有这样好的合作,英国在不远的将来让中国文化通过中国电影的载体走向世界,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问一下编剧们吧,你们觉得现在在电影编剧写作当中你遇到什么问题吗?
兰道尔·华莱士:我觉得有一些部分我不知道下一块怎么往下写了,我觉得这块是特别重要的一块。有的时候我相信那种动力推动者我们,为了得到这种写作的动力,我会把编辑翻过来,把这个剧本最不喜欢的部分写出来。然后我在想想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可能有一些逆向的启发,这就像一种对话一样。
刚才你也说有的时候观众也创造了这个故事,我非常同意,比如写勇敢心的时候,我读了那个书的时候,之所以成为我们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所讲的故事呢?我就想到一个可乐的广告,说父亲和儿子在一起跟他们讲故事,分享它的价值观他的心也他的儿子,告诉他自己是谁,把的儿子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之所以如此我们就来到这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有一个非常传统的文化,也非常悠久和辉煌的历史,所以我们不仅仅要说,而且也要听中国,所以我写故事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说这时候是我倾听的时候,让故事对我说话,所以让我闭闭嘴吧。
布鲁斯·亨德里克斯:实际上你说的非常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我需要让你们导演暗示结束,所以我现在要说,感谢你们精彩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