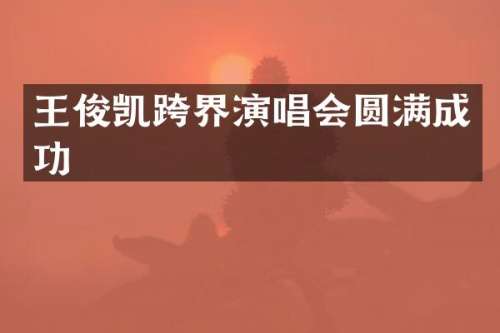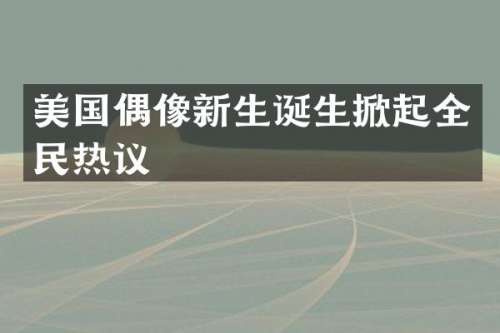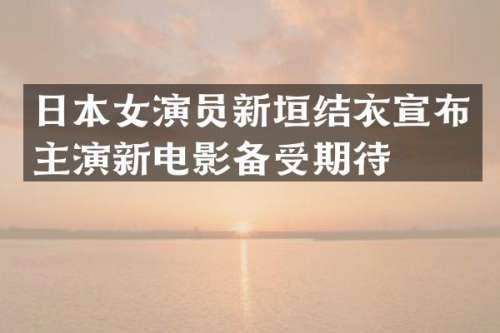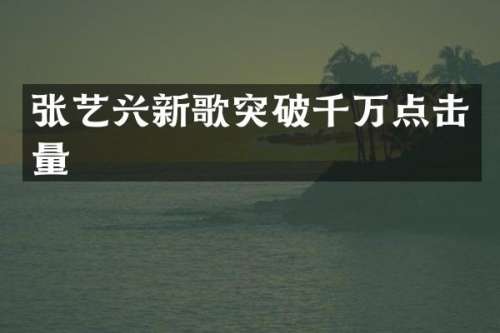几乎没有掀起太多水花,电影《黑客帝国:矩阵重启》(下简称《黑客4》)今天在大陆的院线公映了(流媒体版早在一个月前就已上线)。
作为时隔20年后《黑客帝国》系列的续作,《黑客4》与被奉为神作的前三部曲相比,可谓口碑“扑街”,豆瓣和IMDb的评分都只有5.7分,差评声不绝于耳。
但《黑客4》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于传统的“好莱坞创造力黔驴技穷、只会毁续集”之说,因为在电影一开头,出现了一段亦真亦幻的自嘲——
尼奥还困在矩阵之中(在《黑客4》里,前三部电影被设定为是《黑客帝国》的游戏,尼奥则是创始人),史密斯特工(设定为公司合伙人)则告诉他,虽然他已经在20年前就宣布这个系列完结,但是母公司华纳认为,是时候再做一款《黑客帝国》的游戏续作了,而且华纳与他们的合同里规定:无论他点不点头,华纳都有权力开工。
这无疑是《黑客帝国》系列主创沃卓斯基姐妹埋在电影中的自我解构,好像导演拉娜·沃卓斯基抱着一种与其让别人糟蹋、不如让自己亲手毁掉,“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在创作。
那么,《黑客4》是否真的一无是处,它到底是真正的矩阵重启,还是毁童年的“诈尸还魂”(英文片名为“resurrection”)?时隔20年,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经典的《黑客帝国》三部曲?
01.
黑客帝国:最完美的三位一体
1999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
那一年,互联网刚刚起步,在美国,“dot-com泡沫”方兴未艾,在中国,网络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连后来遍布大街小巷的“网吧”这个词都不存在,当时的叫法,叫“电脑房”或者“游戏室”。
当时流行的小道消息,是一个现在年轻人可能压根没听说过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大约在500年前做出的一个预言:1999年7月4日,“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世界末日到来。
电视机里专门介绍过一个重要的全球性事件:“千年虫危机”。因为计算机计数bug导致的全球危机,那可能是计算机网络第一次以一种具象的形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黑客帝国》第一部于1999年3月24日全美首映。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还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很久以后我才在DVD上看到这部电影,被震得手脚冰凉。到现在,尼奥从矩阵中醒来,看到周围无穷无尽的营养舱的那一刻,仍然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科幻场景之一。
《黑客帝国》(1999)
《黑客1》出现在1999年,有着某种古怪的宿命感,正好在世纪末,一个极为科幻的年份,出现了科幻电影的最高峰(或许没有之一)。
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为《黑客帝国》着迷,从“时间”到“红蓝药丸”,从黑色的皮衣墨镜到绿色的虚拟世界滤镜,黑客帝国贡献了无数经典的美学元素和科幻概念。
《黑客帝国》系列为什么在科幻史乃至电影史上有着如此的崇高地位?答案是三位一体(Trinity):哲学和科幻概念、世界构建、动作场面。
《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开场,尼奥从梦中醒来,正好他的一个客户过来找他拿货;尼奥从一本书中找到了那张光盘,镜头专门给了书封一个特写:鲍德里亚的《仿像与模拟》。
《黑客帝国》是极少数将哲学理念带入大众通俗娱乐的电影,从古典的柏拉图洞穴寓言,到认识论,到后现代的拟像理论,景观世界,这系列几乎无所不包。
它最基本的概念构建在一个思想实验上:缸中之脑。既然人类所有的感觉、体验,本质上都是大脑中的神经电信号,那么,将一个大脑放入缸中,用超级计算机传递电信号,大脑是不是无法分辨,他所体验的到底是真实世界,还是计算机制造出来的虚拟现实?
在电影里,尼奥躺在培养缸里,完全就是这个思想实验的视觉化版本。《黑客1》的主题,是“何谓真实”,讲述一个洞穴寓言,这在商业电影中已经非常难得。
而《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The Matrix Reloaded,2003),并没有局限在这个层面,而是将第一部已经埋好的概念进了一步,讨论的是自由意志和宿命论——一个商业电影不但讨论哲学,在续作中居然讨论的是不同的哲学。
《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2003)
直到尼奥见到了“建筑师”(Architect),才发现一路走来,他的选择是已经被决定的,这实际上用一个很小的桥段就表示得很清楚,锁匠在临死前交给尼奥一把钥匙,告诉他使用这把钥匙可以通向源代码,但是没有告诉他是哪扇门。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知道是哪扇门”。实际上这里的真正意思是,尼奥无论选择哪扇门,都是命中注定,他注定会进入源代码。
建筑师房间内那一面墙的电视,每一个屏幕都代表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尼奥,但是他告诉尼奥,他只有两扇门、两个选择。在这里,宿命和自由意志的冲突,被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The Matrix Revolutions,2003)同样也没有止步于重复前作:尼奥和史密斯的对决,最终史密斯“中和”了尼奥反而被毁灭,这是毫无疑问的东方哲学观念:阴阳相生。尼奥和史密斯都是系统的bug(故障),但是两个bug的结合却升级了系统,光明与黑暗,阴与阳,永无止境的螺旋形上升。
能做到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哲学思考,难怪有大量哲学家会专门撰文讨论《黑客帝国》系列带来的思考。
从世界构建的角度,《黑客帝国》系列也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重点在于这个矩阵内外的二重世界。
在第一部中,尼奥醒来,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的真实样貌,那是最原始的认知冲击。甚至沃卓斯基姐妹在视觉上也做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矩阵之内,世界是绿色的;矩阵之外,世界是蓝色的。
《黑客帝国》(1999)
在《黑客1》中,我们看到了巨大的人类养殖农场,以及永无止境的地下管道;到了《黑客2》,锡安城真正的模样出现了;到了《黑客3》,我们又看到了机器城市,以及乌云遮罩之上的天空——或许那并不是真正的天空,而是另一层虚拟世界。
沃卓斯基姐妹在电影中埋下的各种情节桥段,都刻意进行了模糊处理,“锡安是真实世界还是另一层矩阵”这个问题,直到20年后,仍然有人为此争论不休。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的另一系列杰作,是《黑客帝国动画版》(Animatrix),沃卓斯基姐妹邀请日本动画导演制作的《黑客帝国》世界观下的短篇集。
这些短片,既有前史性质讲述人类与机器战争的《二次复兴》,也有讲述矩阵中觉醒人类的《少年故事》《世界纪录》,还有讲述人类反抗军的《矩阵化》《程序》,每个短片都拓展了黑客帝国世界观,让整个世界构建更加庞大,也更加生动。
从影史角度,他们也开创了“在相同世界观下讲述多样故事”这样一个子类型,足足领先漫威十年。
《黑客帝国》(1999)
至于动作场面,也是《黑客帝国》给整个电影产业树立的标杆:沃卓斯基姐妹不仅首创了“时间”这个特效,也是好莱坞最早引进香港武术指导(具体来说,是袁和平)的动作电影之一。
它开拓性地将一整套香港功夫片的动作美学引入了好莱坞动作大片,自此,充满美感和设计感的武术功架,飘逸的动作,以及拳头击打到脸上的慢镜头,就不再是香港功夫片的专利了。
02.
黑客帝国4:重启失败?
从系列第一部到第四部,已经过去了22年。如果一个婴儿在《黑客1》上映那天出生,那么到《黑客4》上映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大学毕业并开始工作了。
《黑客帝国》成于移动互联网,不,应该是说整个互联网都还没有真正普及的时代。现在的新一代观众,他们对《黑客帝国》的了解,很可能只局限于社交网络上的梗,或者短视频里浮光掠影的片段。
在这个社交网络和短视频几近占据了人们全部的注意力,几乎人人都听说过“元宇宙”的时代,《黑客帝国》所展现的那个虚拟世界,在当下,比在1999年显得更加真切,也更加相关。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华纳才决意要重启《黑客帝国》,给新生代的观众演一遍“老把戏”。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拉娜·沃卓斯基带着《黑客4》,以一种几乎可以称作“破罐子破摔”的心态,直挺挺地摔在这个“重启”的大坑里。
22年前,作为沃卓斯基姐妹的第二部长片,也是第一部科幻片,《黑客1》凝结了两人几十年以来思考和痛苦的结晶:关于缸中之脑,关于洞穴寓言,关于选择与宿命的哲学,甚至还包括两人对自己性别身份倒错的困惑和痛苦……都塞在了这系列电影中,让其有着异常丰富的可解读性。
《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2003)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黑客4》中拉娜·沃卓斯基借着尼奥之口,直接说出了“对我来说,《黑客帝国》三部曲已经完结”这番话。
世界上的天才构思只足够燃烧一次,那之后就只剩下灰烬。《黑客4》想要把这些灰烬收拢起来,塑造成一个好看的壳子,从这个角度,这部电影毫无疑问是失败的。
让我们以同样的“三位一体”标准,来评价一下《黑客4》。
这部《黑客4》相比于《黑客帝国》前三部曲,在科幻概念上没有任何进步,甚至可以说有所退步:仍然是缸中之脑,人被机器所禁锢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要命的是,在《黑客2》《黑客3》中有意模糊的“锡安到底是真实世界还是另一层矩阵”的讨论,在这一部里无影无踪,主创非常简单干脆地放弃了这一点,直接说明锡安就是现实世界,让这部电影的科幻概念退步了不止一个档次。
在世界构建上,这一部电影也乏善可陈:矩阵之内没有看到任何新的视觉元素,连标志性的绿色滤镜都被放弃了;而矩阵之外,这个新的人类城市(IO),除了一个新设定“部分机器也倒向人类一边”之外,也没有任何新的想法。
世界构建的核心要点,实际上在于“不同的人群角色有着不同的目的,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行动”,《黑客帝国》系列在世界构建上的出色,就在于此:
锡安城的长老,其他飞船的船长,甚至包括最基层的平民,他们都有自己的任务,根据自己的想法行动,很多时候也会跟尼奥他们起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真实可信的样貌细节。
而这一部里,包括那些回收再利用的老角色,全部的人物都堪称工具人,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这种“顺拐”的剧情,难以给我们带来任何关于IO,关于机器世界的深刻印象。
至于动作场面,那就只能说真的很平庸了。《黑客1》引发了在好莱坞动作片中加入香港功夫片美学的风潮,20多年过去,这套体系早已过时——好莱坞动作片最新的典范,恰恰同是基努·李维斯主演的《疾速追杀》系列,极度写实的近身搏斗和斗术才是目前流行的风格。
然而《黑客帝国》系列却根本不适用于这种风格:很难想象在前几部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尼奥到了最新一部电影里,就开始玩起综合格斗近身技(MMA)和中轴重锁(Center Axis Relock,CAR技术)战术射击。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2021)
于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尼奥既没有前几部的飘逸和功夫,也没有能力再树立新的动作美学标杆,只剩下了偶尔拙劣的自我“致敬”,外加一个疲惫的、气喘吁吁的中年人不停放“龟派气功”。
看到这个场景,或许前作里雨果·维文饰演的史密斯特工,都会用那种非常特别的语气说一句:“How embarrassing.”(太尬了吧)
03.
红药丸,蓝药丸,还是黑药丸?
那么,是不是要下一个结论,这部《黑客4》一无是处了?的确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但且慢——
《黑客4》开场的三十分钟,是一个典型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沃卓斯基姐妹在电影中直接讨论了发生在电影之外的事情。
尼奥被重新带回矩阵之中,继续作为托马斯·安德森生活——在这个版本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戏设计师,设计了《黑客帝国》这款游戏,并且凭借着游戏拿到了1999年的TGA大奖(The Game Awards,游戏界最高奖项,虽然在现实中这个奖直到2003年才第一次颁发)。
《黑客帝国》前三部曲的内容,就是他制作的游戏。他时常也会被来自过去的记忆所困扰,但是心理分析师告诉他,你的问题是一个艺术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分不清自己的艺术创作和现实。
导演拉娜·沃卓斯基的小心思在这个设定中体现出来,大家见过很多元叙事,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电影中新版史密斯特工说了一句话:将机器世界这么重要的概念,就藏在一部游戏这样看似庸常的事物之中,这个版本机器的手段进步了。
这句话直指这一部《黑客4》,拉娜想表达的核心价值观:前三部曲讨论的,是人类无法认识到何谓真实;而这一部,讨论的是人类其实无所谓真实。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2021)
从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最近十年在美国逐渐壮大的概念:“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wing,缩写为Alt-right)。他们是一群抱持各种各样不同观点,只有在跟美国主流宣传叙事唱反调这点上一致的群体集合。
在“另类右翼”中,什么样的观点你都能找到,既有各类热衷于“蜥蜴人”“脑控”的等概念阴谋论,也有有理有据的批判。
但是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目前主流媒体和舆论环境是一台谎言机器;他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谎言,给民众制造出了一整套的虚拟世界——这与《黑客帝国》中的矩阵非常类似。
《黑客帝国》系列就是这个群体的圣经。实际上,另类右翼常用的术语中,有几个词恰恰就出自黑客帝国:bluepill/redpill/blackpill(蓝药丸/红药丸/黑药丸)。
蓝药丸就指一般大众,没有觉醒的大部分人;红药丸指的是你获得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深刻地揭了主流媒体、网络世界的谎言。吃下红药丸,就代表着你已经觉醒,挣脱出这套谎言机器的叙事;而黑药丸,指的是效力最强的红药丸。
《黑客帝国》(1999)
拉娜·沃卓斯基在《黑客4》的台词之中埋藏的这套世界观,某种程度上是叛离主流叙事的,甚至包含着某种隐喻与批判性。
媒体构建整个谎言世界的方法,并不是严厉打击、删除和深藏真相(就好比《黑客帝国》前作里派出特工到处抓人),而是将真相放在无聊平庸的地方,或者搜索结果的第二页。通过几十年现代传播学的摸索,他们深知,最精妙的谎言实际上是只说出部分真话。
机器意识到,与其封禁叙事,不如塑造叙事,进行“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将“世界是虚拟的”这个事实藏在特工的后面,远不如用温和的,没有杀伤力的方式放在光天化日之下——
《黑客4》的结尾,面对已经觉醒的尼奥和崔尼蒂,分析师的那番发言,实际上就非常接近另类右翼宣言。他同样使用了另类右翼的常用术语“sheeple”:这个词由sheep和people合成。
分析师说,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想要自由,他们想要的是安全和舒适。踏出矩阵之外获得真相,对他们才是残忍的。
而在电影里获得大奖的《黑客帝国》游戏之中。电影里分析师第一次揭开真相,说出了这个版本矩阵控制人的手段:大众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感受。只要被饲喂的他们感觉良好,他们就能够快乐地生活在谎言世界之中。
在《黑客4》最后的那场大战中,矩阵世界中的无数普通人实际上是机器人(bot),如同僵尸一样冲向尼奥他们。这个动作场面实际上是一个隐喻:这些机器人,实际上就是被完毕的民众。
他们相信一整套被编造出来的美丽新世界,能够非常轻易地被媒体“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构建想象中的敌人和仇恨对象。过去20年,美国经历了08年金融危机,战争的泥潭,16年川普当选煽动起的民粹,疫情防疫的各类表现……其中种种,无疑印证了《黑客4》的隐喻与讽刺。
从这个角度来说,《黑客4》的暗喻其实超越了左翼和右翼,也超越了地域与族群,与当今的现实世界高度关联。偏颇的媒体、算法、互联网巨头等等,不也同样带来了巨大的撕裂、同温层和信息茧房吗?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2021)
这说明拉娜·沃卓斯基并没有完全加入好莱坞同温层,而是对这20年里美国社会和政治有所观察,有所感悟,这对于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导演而言,是极不容易的。
同样叛离正统叙事的,还有《黑客4》的结尾:尼奥和崔尼蒂一同跃下大楼,但是真正突破自我、习得飞行的人,不是尼奥而是崔尼蒂——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指引。
不管是拉娜的创作心态,还是上文所述的另类右翼叙事,或许都出自巧合和虚构。但是这里包含着一种女性叙事,无疑是更真实,也是更加自然的。
22年前,沃卓斯基拍《黑客1》的时候,他们还是兄弟;到了今天的《黑客4》,两人已经变成姐妹——实际上整个《黑客帝国》系列,都包含着这种性别身份倒错,转换的困惑和矛盾。
《黑客4》的结尾,则干脆利落地将这点明示了出来:这是一个唤醒“The One”,再来一遍的故事。而谁是The One?实际上是崔尼蒂,而非尼奥。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沃卓斯基姐妹与自己身份的终极和解。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2021)
撰文:思故渊
编辑:苏小七
监制:猫爷